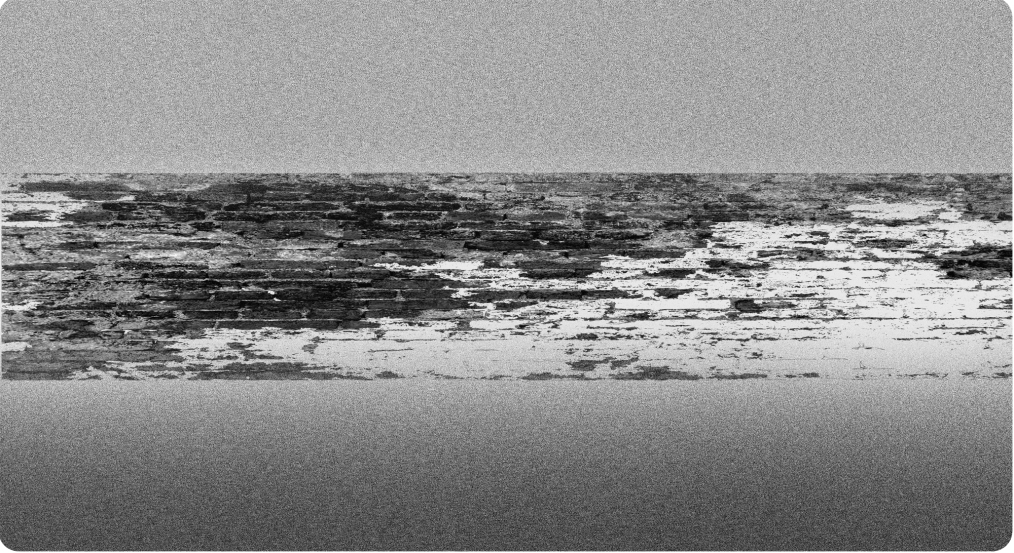香港警察在保護集會自由上的表現與市民的期望,落差日漸擴大。特別在曾經親身參與遊行集會的市民眼中,不滿程度可以用「討厭」形容。
鮮有投入集會的市民,從主流媒體的採訪取材之中,未能了解警察打壓言論的取態,可以理解。但置身當中親身執行的警員作為個體,何以甘心自己成為打壓的機器,同時將自己的身份認同,與作為一個市民的身份區隔開去,此一問題就非常有趣了。
要試著解答這個問題,不妨試思考一下警員的個人心態。不必將警員妖魔化,也不必將之神聖化,因為在相同的情況,化身打壓機器,對每一個普通人而言可能其實都容易之極。
投身警隊的普羅大眾,可能是從保險從業員、市場推廣人員又或是其他尋不過的云云行業之中,相中警察這份職業。與其他職業一樣,考慮的是薪酬福利、工作量、工時穩定等因素。既然待遇可觀,便投考之。另一個特別使人被吸引當上警員的原因,是權威的授予,制服與制度,為警員提供優越感。
有人可能會問:那麼使命感呢?總不能將每位有志成為警員的人,都說成是單為薪水為權威感而當上警察,這樣的說法太以偏概全。
是的,其實還有不少警員都有其使命感,只是那個使命感,在警察龐大嚴密的體制中,絕大部份情況均由上級賦予。
由警校訓練開始,大量講求紀律和服從的去人性化、個人化的操作便一直開展。警校中,自上級對學員的嚴苛態度,以及對其個人性格的侮辱(入過警校的朋友跟我就分享過,考官無理的粗口謾罵是其特色之一),讓他們對權威服從,也讓學員對當上權威,更為憧憬——特別當所有同伴都服從尊崇於這種權威,集體的情緒影響,獨立思考不得不被壓抑。
現在讓我們帶著這種心態構成,回到平常集會示威的現場。市民對警察的失望,在於期望警員以「服務市民及保障其自由為宗旨」的理念,與警員「實際行動上在打壓自由」之間的落差。
但警員工作的環境,會令每位警員心中是以「服務市民」為宗旨嗎?從曾偉雄的言論「執法需要道歉是天方夜譚」中可以看到,警員的思考中,大前提並非為了對等或是由下而上地「服務市民」。反而是將自身的角色,置於一個功能之上,一個維持狀況穩定的、由上望向下的權威功能之上。
現在幻想一下,你正在警署與一眾制服筆直的同儕一同站立,等待上級講解今日遊行的安排。指令是:咪俾「班友」搞到「XXX副主席XXX先生」。指令之中,誰應該服從權威,誰是比你現在服從的權威更權威(即大佬的大佬),暗示清晰易見。聽著這個今日值班唯一可以進行的指令,你當然擔心會俾「班友」搞到遲收工睇唔到場戲。但如何在不得不值班的一段時間,管理好呢班友,你想起了女友昨晚電話提到的一句:「坐喺公司成日無嘢做仲慘,有D嘢搞下但收工前啱啱好搞掂就fit啦。」如何在工時內花心思去做好這個工作指令,是時段內算是比較有趣的一環。
走到街上,遊行市民沒多少好嘴臉,在上級命令的封鎖區內外一直對峙,被示威市民不絕謾罵的情況,已經兩個多小時——一種挑戰你及你那套被賦予權威的制服的動作。戲票變成廢紙是無可逆轉的事實,更麻煩的是上級開始緊皺的眉頭,過去的經驗告訴我,這是一個令人緊張的情況發生的先兆,特別是今次的不悅,是源於上級的上級,即是那位政要。
保護上級是要務,保護上級的上級,就更是穿著制服者更為重要的任務。將一班漠視我們權威的麻煩友除之而後快,一眾同袍誰都沒有異議,你也自然不可能提出也不應思考任何異議。
本身同是市民的身份早已不復存在,「市民」和「我們」,是對立的。早年,被集會市民篤一下即倒下的把戲早不適用,原因在於片段於電視新聞一播出後,雄糾糾的威風又顯得太弱不襟風,損弱了強悍的形象。
又難得現在的大佬那麼的有膊頭,被市民輿論一責斥起來,對內對外都那麼支持一班手足,一陣火燒的感動一直燒到心眼,感到高高在上的他是與自己同在的。對上一次有這樣的感覺,已經是在電影院中,看古惑仔系列時陳浩南就手下殺了對家大佬時,一力承擔的那種干雲浩氣,啊,都多少年了啊。
警員當值時腦裡的心態是這個樣子,沒有可能嗎?警員作為隊伍的一份子,所關心的,可能根本就不是如何維持市民權利,這個時候,就出現了兩者期許上的差異了。
這樣的警員很討厭嗎?先別急著義正詞嚴地罵起來,試想想,在警隊一個這樣組織嚴密地去人性、反對獨立思考的組織之中,閣下投身其中,在群體壓力以及集體思考的常規底下,身體裝進了別具意義的一套制服之內,保持清晰獨立的思考,真的如此容易嗎?
萬勿對自己的自由意志過於自信,畢竟單靠閉氣就能自殺的人,相傳也只有古希臘叫Diogenes的哲學家才辦得到。
明白了在那個圈內尋常人要保持自我意識的困難,下一個問題就是,即便如此,要如何抗衡這種環境影響,去保持獨立思考呢? 以下提出的看法,比較悲觀,可是較為可靠的,卻鐵定是電視廣告中的那句宣傳口號——
「不可一,不可再。」
不去觸碰不去進入那個迷離景界,便不用擔心自身自由意志的薄弱了。也許等到醬缸有一天意識到自己的混濁,再沒有材料肯自願投進來的時候,它會肯變得潔淨一點。
至於已經身在警隊當中的每個個體,在下了班回家休息、一個人獨處的夜裡。當你坐在床沿,身上穿著的不再是制服,而是星斗市民睡覺所穿的T-Shirt 波褲的時候。請攤開手掌仔細端詳一下,上面的掌紋,並非由哪一個權威為你刻下的,紋理支葉分流到人生的哪一個方向,可能性還多得著呢! 更重要的是,拳頭一捏緊,千百個可能都操控在你自己的手心。白天所做的一切,對自己以及所愛的人長遠是好還是壞——原以為多賺薪水為他們好的你——細心再想想,是真的不知道嗎?
真的?